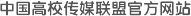- 首页 ->> 2017中国高校新闻扶持计划 ->> 正文
-
逃离马戏团
http://www.xiaomei.cc 2017-07-10
来源:《青春报》 作者:石书蕴
欢呼、惊恐、掌声几乎要把充斥着稻草和粪便气味的马戏团掀翻。在这里,利益与利益相互拉扯又相互躲藏,强调着“动物权益”的人们各执一词。
思维定式在这样的环境里发挥着不可预估的强大作用,可颠覆又来势汹汹让人无法招架。因为受控,镜像就外化了。虎嘶象鸣,没人能事先解释它们,因为人们从不拥有它们。正因如此,你看到的才会夸夸其谈、虚与委蛇又生机勃勃。
真实亦如此。
既然遮掩的面具握不住,干脆扬了它。
王彦豹给人感觉愤世嫉俗,发的文字常常很偏激。“这些动物保护组织,打着保护动物,你知道害死多少动物吗?”
整整一周,他一直拒绝我。换个说法,他在考验。
“这几天其实一直在犹豫。还有没有必要再说这个问题。感觉跟谁说也没意义,说多了也没用。以后不聊了。”
我在等待,而他并未继续说下去,甚至在我们告知面谈后,他也一直保持这种态度。
我们决定去现场。
“你们来看什么!来曝光我们,让我们没法生存吗?”他变得激动,“好多媒体说来采访,结果走后都是各部门来制止!”
“不是你说的,眼见为实?”
“好,我也不怕你来,反正已经这样了。你想来再说!”
直到最终和王彦豹见着面,他才告诉我缘由。他检查了我微信,地区显示是重庆。“我很讨厌的一个动物保护协会的总部在重庆。我看了你的资料。”
(一)
普快火车一路向北,沿途不值得有风景可谈,偶尔掠过两三棵焦黄了的行道树,几乎没有色彩。车厢内空气也糟糕,像混着渣的干海绵,活生生地把人的心情裹在干燥中。
王彦豹所在的游击队扎在临清康庄,一个辖区总面积不足100平方公里的北方小镇。理所当然,我们要在中途下车。
到了目的地,他不肯接电话。不得己,只能短信。
“你在哪个方位?”我们问他。
一段时间后,“你们随便打听,都知道。”
他说得没错,马戏团的气味随风传播,我们接触的人都知道镇里来了马戏团。宾馆前台的蒋玉芬前几天刚去,“演了好几天,我们带自家娃去,有动物表演,好看。”
这原是一块凹凸不平的废地,现在被简易改造成乡镇嘉年华。一路找过去并不困难.马戏团就在那里,一连好几家。
现场情况不太好。巨型喇叭声重重击打心脏。一个脏兮兮的中年人,站在关有东北虎的笼子上麻利宣传:“10块10块,不要拥挤,把零钱拿出来。开演了,来吧朋友们,真正的艺术!”入口的音响扯着分贝循环欧美流行乐,相隔40米也感到头晕脑胀。旁边的两只小黑熊瘫在地上一动不动,另一侧,猴子拽着链子挣扎。
越往前,地越颤抖。
路过一丝不挂的脱衣舞团,我们找到吴桥马戏。粗制的塑料大棚勉强看得清掉色的小丑图案,周围堆满垃圾。
我们买票进场,10元一张。今天站门口检票的是张金海。他在团里资质最老,35年。大家称他金哥。团里动物生病都找他,是经验锻炼的。“我一看那狗熊吐就知道(得了什么病)。”
今天表演三场,张金海卖了76张票,一共760,是全团一天的收入,算是多的,“平时只卖两三百。”他有腰风湿,遇到下雨,帐篷里的被褥全湿,痛得不行。
听到我们是记者,他满是沟壑的眼神里突然闪了丝光。他尝试解释他所理解的“眼见为实”,结果把自己绕了进去。“举个例子,有人说新疆有朵牡丹花,长得太好了。你也是听着,等到你去了,谢了也就那么回事。走的路远采访的东西才多,东西一多肯定有好事有坏事,哎呀这话不能这样说,我说错了。”
他的二姐夫许成光,河北沧州人,这个团的团长,小学只读了3年,学历比张金海低两级。全团30多人,包括大蓬在内的投资花了两百万,每日动物的开销一两千。许成光平均每年回家一两次,“我今年55了,再干5、6年就不干了,一过60身体就受不住。”
许成光很骄傲他的阅历,他说自己有国内唯一坚持下来的大棚团队,“也是受累最大,吃苦最大,受气最多。”他太守旧,在大家都往城市去的那段时间里,他还守着大棚,什么苦都受遍了。妻子也在团里,他俩晚上却分房睡。“我和动物睡一屋,它关在笼子里不自由,你不放放它,它不适应。”流动戏班充满变数,有时车坏了走不了,机器冻了就得拆,野外冬天冷,上厕所没地,洗澡别想。
(二)
棚内约600个座,几近满额,大部分是小孩。舞台旁堆着野草,粪便在草腥和香烟的味道里发酵,让人不敢大口呼吸。这不是一个适合动物生存的地方。
上一场刚结束。灯光下,一头4吨半,戴头花的30岁成年雌象碰碰,呼扇着耳朵,规矩地用象鼻接送一个个观众,王彦豹站在旁边,收钱拍照。平均5秒1次,10元1张,这是他在团里唯一的收入来源。
他认出坐在破旧塑料席上的我们,到后台确认,“拿相机的是你们吧”,又执意要求我们看完全场再采访。“你自己看看,有谁会干这个,哭都没法形容了。”马术杂耍、小狗钻圈、狗熊跳绳、大象跨人、磕头送福…每一个马戏表演,都引来一阵欢呼和惊恐。
他穿得很灰,全身浸在深色调里,就像他这段时期的心情,最好别惹他。合影差不多,他跨出舞台,径直过来,说出第一句话。“你们没来之前我恨死你们了。每年这种东西太多,一开始我以为你就是在套话。找噱头,找卖点,后来感觉你还有诚意,不像那种人。其实我也是考验你们,所以我说要不来看吧!”
他带我们去后台。拉开塑料幕帘,从有狗熊、狮子的笼子经过时,他停下来指着说:“你看看,这些都不让表演,从动物园出来瘦成那样没人管,我们不敢扔,只能关起来跟团走,慢慢等死。”
后台是一大片荒地,遍地废弃物。编织袋、坏胶鞋、吃剩的盒饭和破衣物。团里人住在灰不溜秋的简易帐篷内,姑且当住所。王彦豹的紧挨着碰碰。他说,这是为了方便晚上照顾它。
一进蓬内,地上都是土,空间压抑得慌,堆满的饲料味散发出来,很刺鼻。膝盖高的饭桌上残留个冷馒头,花生壳和崂山啤酒。左侧空地上放有跟了他20年的大箱子,和他一起从动物园被赶出来,右侧铺有单人床,他睡觉的地方。
王彦豹35岁,生于杂技之乡吴桥,爸妈都是农民。当地有句民谣:“上至九十九,下至才会走,吴桥耍玩艺儿,人人有一手”。传统环境让他从小受到熏陶。15岁时,杂技团招人,他跟着哥哥跑去面试。“我也是调皮捣蛋,学习不太好,就说我也去玩。”什么也不会的他被相中,哥哥落选。
初中没毕业的王彦豹进了团。在老家练了半年,又去济南三年。出师后有了工资,350元每月,算是最高,他还嫌不够。怎么办。团里有大象,大象吃草,需要打草,一天四五百斤,割一天给50元。为了赚外快,一有时间他就去割。他开始和大象接触,久而久之,他决定半路出家,转练马戏。
碰碰是泰国亚洲象,10岁时由泰国师父从泰国带来,个头和他差不多。碰碰刚来,只听得懂泰语,他也“俗得噶”、“马鲁”地和它沟通。它认人,感情培养很重要,王彦豹喜欢它,和它说话,天气凉烧热水给它喝,碰碰吃饭懒,他捧起饲料送它嘴里;吃饭过年叫上队友给它包饺子,“它其实不吃饺子,但我也给它,不吃它就扔了。”遇上放鞭炮,它胆小,他把手伸嘴里摸它舌头,划一下鼻子,搂着它,“有我们在身边,它会好受一点。”
有次,王彦豹差点死它手上。他带着碰碰下河洗澡。河深,碰碰都够不到底。大象爱玩,一见水乐得不行,看到他也下来,咚咚咚地过来想亲近,不小心过了头,一下就把他压水下。王彦豹进了水,呼吸也困难,好在挣扎中有个空隙,他就喊起来,碰碰听到声响,赶紧把他从河里托出来。“它最顾人,特懂人性。冬天天冷,我们晚上给它生火,它不会冻着。其实大象怕火,你一点火,它会把火吹灭。但是我们给生火,它知道怎么回事。”
(三)
中国早期的马戏表演是流动式,团队全年往返于全国乡镇,长期颠簸,不利动物生存。1996年,王彦豹所在团队与动物园建立合作,开始在园区进行表演。
景区常驻形式,对行业而言是种进步,这表示员工不用居无定所,有自己的宿舍,放假时能把家人带来待几天,动物不用在外运输,特制的水泥房,冬暖夏凉,行动随意,外面还有广场,白天在外晒太阳,晚上回屋睡觉。专业的兽医、医疗设备和安全器械,表演场地和体量也有控制,驯兽师的工作变得类似饲养员,主要负责照顾动物安全。早晨起来,驯狗熊的遛熊,驯猴的遛猴,驯虎的放虎,每天观察其生理情况,一个礼拜给园舍消次毒。除此之外,就是繁殖。哪个动物该发情,就不让它演出,挑一只不近亲的交配。“多享福,它们享福,我们也享福。”
那时候太风光。所有马戏团都以动物数量为荣。“那时繁殖动物太多了,一年好几笼,成活率基本在90%以上,所有的公园都能繁殖。你说,有几个老虎一胎能生6个的,都是我们人工抱养。野生老虎生下来必须管,不管就死定了。”20几个人,三个人每两个小时一班来回倒,6个小老虎要吃奶,虎妞的奶头就那几个,这两个吃完以后翻过来再吃那边,“它们得吃多长时间,但那几个全成活了,我们费了多大心血。动物园谁管你繁殖,多一个还多吃肉呢。现在的老虎至少比前几年的少一半,繁殖了都没人要。”
他不止一次接到官员要虎皮的电话,“你有大猫吗?”十几万,几十万,好多动物园私下都有这种交易。“有些动物园比我们黑多了。我承认我们行业的败类也多,那些个没证没户口的小团体。但我的,你想都别想。”
(四)
稳定归稳定。随着相关表演事故的报道越来越多,民众的动物保护和福利意识的增强,动物表演项目开始不太平。终于,阶段性崩盘。
2010年7月,林业局发出通知,停止野生动物与观众零距离接触、虐待性表演;同年10月,住建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园管理的意见》,要求立即清理整顿住建部所管辖的动物园和公园的各类动物表演项目,发布之日起3个月内,各地动物园和公园要立即停止所有动物表演项目;2013年7月住建部再次出台《全国动物园发展纲要》,明确指出杜绝各类动物表演。
这在胡春梅看来是好事。“当时沈阳动物园有老虎被饿死,触动了相关的主管部门,开始考虑动物的福利问题。[这一段的两个小分句其实上文都提过了,删掉也不影响吧]如果城市动物园没有这些表演,也依旧可以生存。”
胡春梅是动保志愿者。大学时开始关注动物保护福利,她回老家进行了调查,“我发现表演动物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过得那么好,看起来漂亮不等于漂亮,它们其实并不想做表演。可能马戏团的人比较了解动物吃什么,还有小毛病之类的治疗。但我们关注的是动物需要什么,而不是我们给它们什么。”
从动物医学专业毕业后,胡春梅全职投入“拯救表演动物项目”组织中。一个成立一年多的动物保护组织。经费来源主要通过自助和众筹。根据团队调查,全国31个省市目前共有412家动物饲养单位,其中162家存在动物表演。志愿者通过交流,实地考察,发起呼吁,写公开信,向有关部门举报。“目前成效还不错,叫停了天津动物园重新启动的大象表演,杭州也停止了陆生动物表演,还有很多流动马戏团有更好的规范,电视台也不可能随意地动物表演。”
(五)
对马戏团而言,文件犹如晴天霹雳。
完了,砸了。动保组织投诉到住建部,住建部打电话给园区,领导把马戏团负责人都叫去,“你看,下文了。撤。”
停止所有表演。先是老虎,然后狗熊,再到狗羊,最后大象也不行。
碰碰又怀孕了,这是它的第三胎,在园区怀上的。象的孕期有两年,妊娠动物禁止运输。而命令又是强制,所有动物都得走,它不能留。
园长想保护他们,试图把大象藏起来。“你这人都散了,动物没处去,肯定都死了,就留这儿,有问题我盯着。”
后来盯不住。住建部接到举报,“为什么这头大象还在这里?赶走!”
“他为什么能说出‘为什么这个大象还在这里?’你想让它去哪里吗!”
他们感觉自己像没爹娘的孩子,联名向林业局反映,没有任何答复。“民不与官斗,斗得过么?他们一说让我们走我们就得走,领导跟他们瞎说我们也得听。”
迎接他们的是更大的绝望。“我没办法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他们被下达了“死亡诊断书”,本想尽量多躲一会,最后他们不得不接受立即撤走的通条。
他们同样躲媒体。马戏团的消息通过嘴巴传出。不因别的,就怕被举报到当地住建部和动保组织。“我问那些记者,你赶跑我们,动物怎么办?他们说‘是啊是啊,我们也替你们着想’,但报道出来就是那里不让演出了,他们就是看热闹,看什么时候赶走。大象一天吃多少草谁知道?吃多少料谁知道?作息时间谁知道?动保组织知道?你来管啊!整天就是不允许,不允许,只是不允许。到最后真是到哪儿哪儿赶,动物不允许买卖,那动物去哪儿了?所以这个问题我没法跟你说数字,肯定大批大批的没了,都没了。”
他们站在风口浪尖,感觉自己像贼一样,到哪儿都低头。他们害怕手机闪现的陌生号码,看见相机就条件性紧张。他们只好游击战,在信息不发达的农村出没。最后,他们跟着动物一头扎向那些流动之地了。这种营地是小偷、流氓、罪犯和无赖的圈头,但却比其他大中城市的一通举报电话来的安全。越往里走,流浪之旅愈发沉重,最后停在某片空地上,花上两天时间搭起一个棚,表演个四五天。时间一长,当地人没了兴致,他们又迅速转场,绝不停留。
他们对社会的信任也开始瓦解。在他们的江湖认知里,没有废话连篇,没有礼仪可言,除了当地地痞,什么也没有。十有八个会不买票,自己只有忍气吞声。
张金海今天被人拽了脖领子。“想演不,不想演给你停了。”
“那个人说我什么?说我‘和气生财’说我!什么局长混混我都接触过,我说,这是现代社会,一巴掌打不好还得花钱,要搁十年前,我早翻了他。”
“你们就没想过转行?”
“我们这帮都是粗人,有文化谁会干这个。现在出去的生活都苦,男的基本就是跑大车。”
王彦豹冷笑,“要不是怕它(碰碰)死,我早回家了,我儿子现在都不愿意我回去。”
(六)
我们问,有无推荐的行业典型,他们提到同一人,于金生。
“于团,风风雨雨不容易。”许成光说。
“于老板现在欠了好几百万,你知道吗?”王彦豹加了一句。
2013年10月,济南生态公园计划举办动物狂欢节,遭遇一片声讨,住建部连夜致电,在演出前一天叫停。
广告投了八九十万,建房子花一百多万,加上运输和食宿费,损失惨重。“他们打得我们措手不及啊!”住建部主管领导中午找到公园,下令必须天黑前全部搬走,动物一个不留。
时年60岁的于金生再也绷不住自己的情绪,那天晚上,他没有睡着,难过得哇哇哭,导致后来一想起这事,“百感交集,说不出那种苦辣。”
于金生拒绝了很多次采访请求,他说,这叫“引火烧身”。他走路跛脚,是34年前马术表演留下的伤,重心在左,一深一浅。一坐下,他就把左脚翘起,取下老花镜开始打量,右手手势一扬,身体往前倾,他开始说话,一口浓重的吴桥话。
“动物保护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它绑架了政府,让住建部下发公文,跨行业地排斥我们。”
于金生出生于吴桥第十九代杂技世家,兄弟四人。他五岁练杂技,因家计困难,小学没毕业就开走江湖。
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是中国马戏最辉煌的时期。1979年,他成立全国第一个民营杂技团,拿到文化部下发的演出证和林业部下发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证,开始天南地北地演出。上过春晚、获邀出国、承包比赛,最多一年演出六百场,员工四百多,动物几百只,2000年承包中国马戏团,年收益一度近三千万,是中国最大的“马戏大王”。
“三十年的辉煌,三年就破灭。”十多个马戏团,只剩下两三个存活,人走了三百多。员工工资平均五千到一万,现在,他一个子儿也拿不出来,还欠了几百万的债。“欠的这些帐,得重新走江湖才能还。”
行业本身就是江湖。有时需要吃拿卡要,礼送不到就不给办。“现在办个事,说实在的,尽量特事特办,跟主管部门打个招呼,不然就不能办痛快。闯江湖这东西,我们还是懂的,就是常规性的礼节。吃江湖饭,必是苦命人。”
于金生是河北省政协委员,曾提过发展中国马戏的提案。“内容是加大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文化内涵,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结果也很好啊,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对我们的投入也很大。”
他坚称马戏为传统民族文化,是一门艺术。“《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里就有一条叫‘积极饲养,合理利用’,这是国家支持的,是国家承认的民间艺术,存在了几十年,祖祖辈辈,多少代人呐。它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也不敲诈勒索,它是靠艺术吃饭。老百姓都爱看,我们给他们带来快乐。我们挣了钱也去慈善。”
他越说越激动:“你们去问问吴桥的人。我们做的好事坏事,我们自己说那叫自夸,通过别人的口碑才是真实的。”他太恨动保组织,认为他们是假善良,“很多善良的人捐了很多钱给他们,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地把这些钱用在保护动物上。有很多国外的组织潜到中国,来骗善良的中国人。”
胡春梅手机里有全国七八十个相关部门的电话,但马戏团的,没几个。
这个情况在于金生那边得到相同答案。
“没有。”
2012年3月,于金生参加东方卫视一档节目,与动保组织直接交锋。一度失控。动物保护学者莽萍拿着铁质的象钩上场,“这是凶器,是用来殴打大象让它来服从暴力的刑具。”
我们在康庄也看到象钩,问过许成光。“你拿那东西,也不敢吃劲,一吃劲它不就破了吗?破了还得上药还得管。这么大的东西,不知道怎么办它,就给它一下,起一个引导,得有一个驯它的工具。”
于金生回答类似。“全世界的驯象师都有象钩子,一旦大象受惊,就要用这个把它降服。那上面的钩子,可以钩它任意一个地方,不会伤害到它的皮肤,它的皮很厚的。”
因为无法上升到文件层面,那次交锋没有结果。
他开始受到网络抨击,变得低调,但仍不认同所有说法。“你说你保护,你把你工资拿出来。这些人都神经病,我没时间跟他们吵。他们对这个行业不了解,本身就排斥。按照他们的逻辑,这个行业从中国消失,所有的动物都回归大自然,现实吗?别说在中国,在全世界,所有动物都回归,可能吗?已经没有那环境了。”
于金生享受掌声、欢笑,来者不拒。他还做着马戏梦,信念坚定得像某种宗教。“国外那些马戏团,美国玲玲,加拿大太阳,英国皇家…我不服,我就想做出中国品牌,做一流的大马戏。我觉得我这辈子对得起这个行业。国家能让马戏存在,那我放心。我生命不息,憧憬不止。我活一天,我就要为这个事业奋斗一天。只要我人在,我就不会懈怠;只要我有口气,我活着干,死了算!”
(七)
我问王彦豹,他怎么理解“虐待”。他吸口气,大手在膝盖来回摩擦。“我想做个好的驯兽师。我那只老虎养得跟猫一样,那是打的吗?这在动保组织看来是虐待。把老虎养得失去本性,有段时间我也纳闷,这是虐待吗?又不是野化训练,野化的话,我可以让它去咬人,随便咬,绝对更凶猛。它本可以在野外生存,可现在已经没有空间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给它创造一个生活环境?难道非要把它放野外去?放野外就能生活好?不一定吧,野外的狮子老虎成活率很低的,生十个能活两个就不错了。我们驯化它,让它做点儿动作,找个饭碗,吃上口饭,住得好点,难道这也错?你们没事调查下这些动物组织,看他们的资金来源,我听说他们可有钱了,超有钱,是吧?”
蒋劲松是清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素食主义者,《反虐待动物法》的咨询专家,目前致力于动物伦理学的研究。我向他转述马戏团的情况。
“不是所有的传统都是神圣不可改变的。传统本身就在不断变化。随着动物伦理学的发展,这种传统的合理性会越来越受到质疑。他们始终是以盈利为目的,不尊重动物权益,不考虑动物福利,迟早要取缔。”
他反驳了马戏团对动保组织的看法。中国的动保组织其实很缺钱,但在外看来,总是来势汹汹,显得力量很庞大。
“动保组织才应是最弱势的,经费紧缺,两方(有关部门和马戏团)不讨好。现在扭曲了,传递的是完全颠倒的社会形象,这是种误导。”不过他也承认,国内目前确实对马戏团本身和动物后续规划等关注不够,“大家都是弱势群体,动物保护是边缘话题,在民众的认知层面本身就不受重视。如果双方加强沟通,对问题解决可能有帮助。”
“所有的动物表演,不尊重动物天性的,都具有虐待性。”胡春梅说,动物违背了自然天性,不是其正确的生活方式。对观众而言,表演接收不到任何证明的科普知识,只是作为娱乐方式,而现在根本不需要以伤害动物来获得欢笑。
根据拯救表演动物项目组织的调查,中国目前动物安置的草案还未公布,这是个不好的信号。“马戏团的动物来源和死亡去向不为人所知,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国外动物园以救助收容为主,社会也存在救护中心收容非专业性的饲养机构。我们一直呼吁建立动物档案,希望马戏项目的规模得到控制。我也希望更多的马戏团能够转移,这也许是他们未来的出路。”
(八)
王彦豹坚持留我们晚饭,还叫上许成光和张金海。
一坐下,他迫不及待地介绍我们。“他们买票进来的,给我打俩电话都没接,我就不接,就看你们是不是拿记者证进来。”
他们在热气蒸腾的饭馆里灌白干。面上也变得红润,兴许是酒到兴上,连称谓都懒得管,一口同志,又一口侄子侄女;他们扶头、比手势、眯着眼睛;他们希望你听着,最好予以回应,遇到某个话题聊不下去,就干脆以干杯结束,然后是喝酒,喝酒,喝酒。
好久没有这么痛快过。他们开始不顾一切地打开话匣。
知道我们的祖先是谁吗?
“杂技祖先是吕洞宾,我们的祖先是关公。我们都敬关二爷,讲义气!”张金海醉了,“来,二位侄女,侄子,我爷爷就是关公。”
酒气在酝酿,饭局最后,成了三人的独白。
“大风大浪锻炼而来 ,就和那鸟一样,什么天我们都可以飞。”
““他们说我们把脚趾头绞了,成天在外流浪,这脚趾头能好吗?咱这大象,以后就放起来。大象放冰箱分几步,待着!这样就不虐待它。”
“我给你们说个事,你们在北京,中国的首都。咱中国现在还有太多困难的地区,池水用小罐,从石头溪里崴。80岁的老头老太太,我们过去演出,他们看见都说,我活了80,没见过什么叫马唱戏?你们不是马戏团吗?他说马会唱戏吗?他从没见过火车,没见过火车,明白吗?听懂了吗?”
(九)
周末结束后,这次的游击场地就要马上拆除。时间原因,我们无法留到那天。
“我就说明天不走啊,你就看看我们搬家,感受那个花花的眼泪啊,感动地哗哗的。”
第二天傍晚,王彦豹发来了照片。
11月份,天空阴着,下着小雨,拆掉的大棚骨架横七竖八,平地荒凉。
【责任编辑:聂亚栋】相关新闻